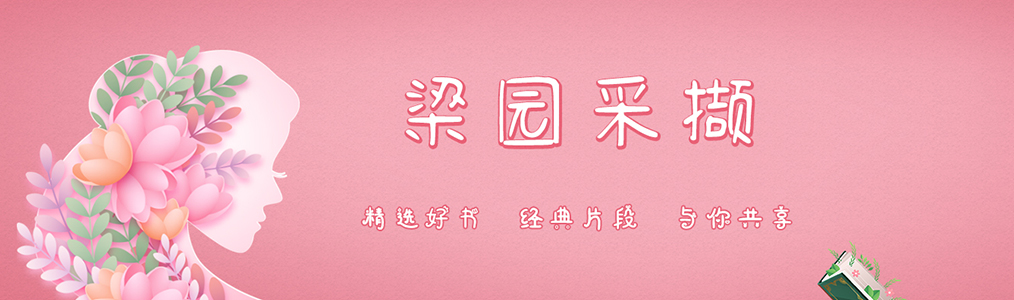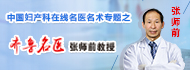流行病学
主持人:王教授您好,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输卵管卵巢脓肿的流行病学情况,以及它对患者的健康危害。
王光花教授:盆腔炎症性疾病是女性的常见病,主要包括子宫内膜炎、输卵管炎、输卵管卵巢脓肿及盆腔腹膜炎等。当疾病主要累及卵巢、输卵管及其周围的盆腔脏器,在局部形成脓肿时,即称为输卵管卵巢脓肿(简称TOA)。可以说,输卵管卵巢脓肿是盆腔炎中较为严重的类型[1]。
据估计,输卵管卵巢脓肿在盆腔炎中约占10%~15%。作为盆腔炎的一种类型,输卵管卵巢脓肿好发于性活跃期的育龄女性,它的主要危险因素包括多个性伴侣、既往有盆腔炎病史、存在性传播疾病、使用免疫抑制剂,以及患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等。另外,某些宫内节育器也可能会增加输卵管卵巢脓肿的风险[2]。
输卵管卵巢脓肿对患者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在急性期,除了局部炎症表现之外,还可以引起多种并发症,甚至造成潜在的生命威胁,比如脓毒血症、脓肿破裂等。
如果诊断或治疗不及时,则可以导致多种长期后遗症,如慢性盆腔痛、盆腔炎反复发作、盆腔粘连、不孕症和异位妊娠等[3,4],在临床工作中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临床表现和诊断
主持人:输卵管卵巢脓肿的临床表现和诊断依据主要有哪些?与其他类型的盆腔炎有什么不同吗?
王光花教授:总的来说,输卵管卵巢脓肿的临床表现更为严重,但缺乏典型症状。与其他类型的盆腔炎症性疾病相似,最常见的表现为持续性的下腹痛,伴活动或性交后加重,发热、白带增多或伴有异味等也较为常见。
病情严重者可有寒战、高热、头痛、食欲不振等全身症状,或恶心、呕吐、腹胀、腹泻等腹膜炎症状;也可出现尿频、尿痛、排尿困难等膀胱刺激症状,或里急后重感、排便困难等直肠刺激症状[2]。
体格检查时,可出现下腹部压痛、反跳痛及肌紧张等炎症表现。需要注意的是,输卵管卵巢脓肿多数是单侧的,但也可能是双侧脓肿。
妇科检查时,可见子宫颈黏液脓性分泌物,伴有子宫压痛,或附件压痛,或子宫颈举痛等表现,或于附件区触及包块,且压痛明显。
在实验室检查中,C-反应蛋白水平是诊断输卵管卵巢脓肿的重要指标。有研究显示,在有盆腔炎症状的患者中,当CRP浓度超过49.3 mg/L时,预测输卵管卵巢脓肿的特异性为93.4%,敏感性为85.4%[5]。
除了CRP之外,白细胞计数、红细胞沉降率也有助于诊断输卵管卵巢脓肿。超声检查、盆腔CT或MRI 检查等辅助检查有助于确诊输卵管卵巢脓肿[6]。另外,应当及时采集分泌物等标本,进行细菌培养和药敏检查,以指导抗菌治疗。
病原体与抗菌治疗
主持人:输卵管卵巢脓肿的主要病原体有哪些?抗菌治疗方案该如何选择?
王光花教授:与其他类型的盆腔炎症性疾病相似,输卵管卵巢脓肿主要为上行性感染,淋病奈瑟菌等性传播病原体是主要的致病微生物。多种需氧菌、厌氧菌、沙眼衣原体、生殖支原体等也是输卵管卵巢脓肿的常见病原体,且多为混合性感染[6]。
目前,抗菌药物保守治疗仍然是输卵管卵巢脓肿的一线治疗。由于病原体较为复杂,且往往难以明确病原体,所以通常为经验性使用广谱抗菌药物联合治疗,或使用莫西沙星单药治疗。
由于细菌耐药性不同,各个国家或地区在药物选择方面也有所不同。比如,由于淋病奈瑟菌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率较高,美国CDC并不常规推荐含喹诺酮类的方案,而国际性病控制联盟及欧洲指南中推荐的含喹诺酮类方案则相对较多。
我国《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规范(2019修订版)》中推荐以β-内酰胺类,或喹诺酮类,或β-内酰胺+酶抑制剂类广谱抗菌药物为主,联合米诺环素等覆盖非典型病原体,同时联合硝基咪唑类药物覆盖厌氧菌[7]。
在硝基咪唑类药物方面,甲硝唑无疑是最经典的药物,但是我国已经有了更多更好的选择。比如,我国原研的吗啉硝唑,就具有抗菌谱广、抗菌活性强、消化道和中枢不良反应少等多方面的优点。
抗菌治疗的疗效影响因素
王光花教授:文献报道显示,输卵管卵巢脓肿抗菌治疗的成功率约为70%~75%[2]。这也就意味着大约1/4~1/3的患者需要从抗菌治疗转为手术治疗[8]。
影响输卵管卵巢脓肿抗菌治疗成功率的因素,或疗效预测因子,仍有一定的争议。2019年,新加坡的学者发表了一项针对亚洲人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共136例输卵管卵巢脓肿患者纳入研究,结果显示,抗菌治疗成功率为81.6%,另外18.4%的患者转为手术治疗。这一研究发现两个独立的疗效预测因子。
第一个独立的疗效预测因子是脓肿直径。这一研究发现,脓肿直径的疗效预测折点为7.4 cm,当脓肿直径超过7.4 cm时,每增加1 cm,抗菌治疗失败率就会增加1.28倍[8]。其原因可能是当脓肿直径增大时,抗菌药物更加难以穿透脓肿区域。
这一结果与西方国家的研究类似。比如,美国的研究显示,脓肿直径为8 cm时,抗菌治疗失败率约为43%,而脓肿直径超过10 cm时,抗菌治疗失败率则可达到60%。
第二个独立的疗效预测因子是体质指数(BMI)。这也是近年来一个新的发现。其原因可能是BMI影响抗菌药物的分布和代谢等体内过程。这一研究发现,当BMI≥24.9 kg/m2,也就是达到超重标准时,BMI每增加1 kg/m2,需要手术治疗的风险就增加1.1倍[8]。
穿刺引流
主持人:您刚提到抗菌治疗效果不好时,可以考虑穿刺引流,那么穿刺引流在治疗输卵管卵巢脓肿中的效果如何?
王光花教授:随着临床影像学的发展和穿刺引流技术的进步,穿刺引流术成为输卵管卵巢脓肿的有效治疗方案之一。
正如刚才所说的,单纯抗菌治疗TOA患者的失败率较高,而对于需要从抗菌治疗转换为手术治疗的患者来说,住院时间、手术并发症、总的抗菌药物使用时间等均会明显延长,从而影响最终疗效。
穿刺引流具有创伤小、操作简便等优点。对于急性炎症期,伴有高热或心、肺等重要器官功能减退,或其他原因导致对手术耐受力较差的患者,穿刺引流是一种较为安全、方便的选择。
2020年发表的一项系统回顾研究发现,在纳入研究的975例TOA患者中,406例,也就是42%的患者在抗菌治疗的同时,接受了超声或CT引导下的穿刺引流,其治疗成功率为90%~100%,明显高于单纯抗菌治疗组的65%~83%,也高于腹腔镜下穿刺引流组的89%~96%。同时,穿刺引流组在并发症、住院时间等方面均具有更大的优势[9]。
在使用穿刺引流术治疗TOA时,需要注意,其疗效与治疗时机具有密切的关系[10,11]。在脓肿形成的初期,细菌大量繁殖,炎症反应明显,此时进行穿刺引流的效果相对较好。而在炎症的慢性期,病灶局限化,细菌增殖减弱,逐渐形成厚壁脓肿等病理改变,穿刺引流的效果则有所下降。
所以在诊断TOA后,除了应当及时给予抗菌治疗,还要积极考虑穿刺引流以提高临床疗效。
手术治疗
主持人:除了穿刺引流之外,有时候我们还需要依靠手术治疗输卵管卵巢脓肿,那么手术时机、手术方式应当如何选择?近年来在手术治疗方面有什么新的研究进展?
王光花教授:近年来,临床上对于包括TOA在内的盆腔脓肿患者的治疗模式,逐渐由单纯药物治疗转变为手术干预,腹腔镜手术则是最常用的方法[12]。手术治疗时机尚无统一标准,可以参照我国《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规范(2019修订版)》中推荐的手术时机,包括紧急手术和择期手术两类。
紧急手术又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药物治疗48~72小时,体温持续不降、感染中毒症状未改善或包块增大者;另一种是怀疑脓肿破裂,患者可表现为突然出现腹痛加剧,伴有寒战、高热、腹胀等。
择期手术主要针对经药物治疗2周以上、包块持续存在或增大的患者。
手术治疗原则上以切除病灶为主。年轻或有生育需求的患者,应尽量保留卵巢功能;年龄大、双侧脓肿或脓肿反复发作的患者,可以行全子宫及双附件切除术。
关于TOA患者的手术治疗,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随机对照研究,一些小规模的研究支持早期手术治疗。
比如,2020年发表的一项针对TOA患者早期手术治疗的5年回顾性研究,结果显示,在50例符合标准的TOA患者中,31例,也就是62%的患者接受了早期手术治疗。另外19例,也就是38%的患者接受了初始抗菌药物治疗,其中12例治疗成功,7例转换为手术治疗。
早期手术治疗的成功率为96.8%,随访12个月的再入院率为16.1%,均优于转为手术治疗的患者。因此,这一结果也支持早期手术治疗[13]。
【小结】感谢王教授就输卵管卵巢脓肿这一话题为我们所作的精彩介绍。从王教授的介绍中可以看出,输卵管卵巢脓肿是较为严重的盆腔感染,单纯抗菌治疗的失败率相对较高,针对抗菌治疗预测效果不佳的患者,比如脓肿直径较大、超重或肥胖、CRP较高的患者,应当及早进行穿刺引流或手术治疗。
参考文献:
[1] S. G. McNeeley,. Mazzoni et al. Medically sound, cost-effective treatment for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and tuboovarian abscess. American 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ecology, vol. 178, no. 6, pp. 1272–1278, 1998.
[2] C. A. Chappell and H. C. Wiesenfeld, “Pathogenesis,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of severe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 and tuboovarian abscess,” Clinical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vol. 55, no. 4, pp. 893–903, 2012.
[3] C. Chayachinda and T. Rekhawasin, “Reproductive outcomes of patients being hospitalised with pelvic inflammatory disease,”Journal of Obstetrics & Gynaecology, pp. 1–5, 2016.
[4] M. Trent, D. Bass, R. B. Ness, and C. Haggerty, “Recurrent PID, subsequent STI,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outcomes: Findings from the PID evaluation and clinical health (PEACH) study,”Sexually Transmitted Diseases, vol. 38, no. 9, pp. 879–881, 2011.
[5] Rachel Ribak. Can the Need for Invasive Intervention in Tubo-ovarian Abscess Be Predicted? The Implication of C-reactive Protein Measurements.
[6] 盆腔炎症性疾病诊治规范(2019修订版).
[7] 张岱. 盆腔炎的诊治进展. 临床药物治疗杂志, 2019,17 (12): 36-39, 69.
[8] Grace Ming Fen Chan, et al. Tubo-Ovarian Abscesses: Epidemiology and Predictors for Failed Response to Medical Management in an Asian Population. Infect Dis Obstet Gynecol. 2019, 2019: 4161394.
[9] Oluwatosin Goje, et al. Outcomes of Minimally Invasive Management of Tubo-Ovarian Abscess: A Systematic Review, The Journal of Minimally Invasive Gynecology (2020), doi: https://doi.org/10.1016/j.jmig.2020.09.014
[10] Farid H, Lau TC, Karmon AE, et al. Clinic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Antibiotic Treatment Failure for Tuboovarian Abscesses [J]. Infect Dis Obstet Gynecol, 2016, 2016: 5120293-5120300.
[11] Silva F, Castro J, Godinho C, et al. Minimally invasive approach of tubo-ovarian abscesses[J]. Rev Bras Ginecol Obstet, 2015, 37: 115-118.
[12] 李咏梅, 等. 盆腔脓肿的临床特点和诊治分析.临床医学, 2018,3: 72-74.
[13] Stephanie Zhu, et al. Impact of early surgical management on tuboovarian abscesses.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aecology, DOI: 10.1080/01443615.2020.1821620.
 妇产科在线APP下载
妇产科在线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