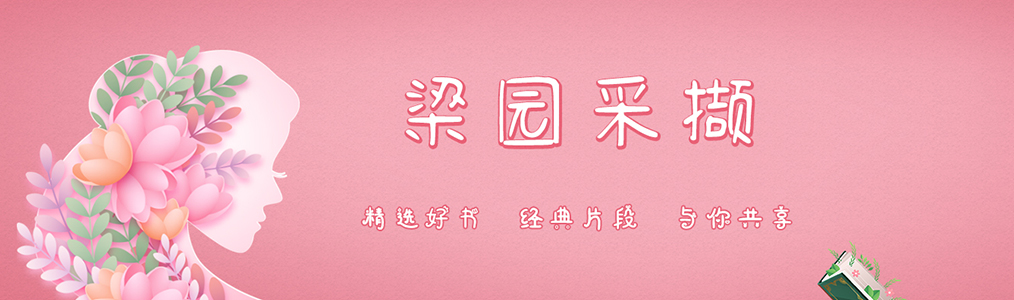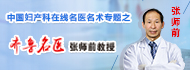摘要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围生保健的系统化,早产儿/低体重儿存活率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由于其发育障碍明显增加和其他不可知的预后,同时又带来一系列社会和伦理问题。对于极度早产儿或极低体重儿是否予以救治的问题,医学和社会学观点一直存在争论,对早产儿存活现状、关于早产儿救治的若干态度和面临的伦理学尴尬作一综述。
关键词 早产 婴儿 伦理学
早产儿又称未成熟儿(preterm infant; premature infant),指胎龄不足37周的活产婴儿,常与母亲孕早期疾病、外伤、生殖器畸形、过度劳累等有关。低出生体重儿(LBW)指出生体重不足2 500 g者,不论是否足月或过期,其中大多数为早产儿和小于胎龄儿。凡体重不足1 500 g者又称极低体重儿(VLBW),胎龄不足32周者称极度早产儿。
随着产前监护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儿科医学的飞速发展,早产儿的存活率大大提高。早产产生的原因复杂,影响早产儿生命质量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其存活增加又可能带来一系列发育障碍和社会问题,所以早产仍然是最主要的挑战和最有价值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全面探讨早产对儿童自身和对社会的影响,尚需从伦理学的角度思考。
1 早产儿存活现状和长期预后
诊断、治疗技术的进步,围生保健的系统化和社会环境因素的改善对心肺复苏后的极度早产儿或极低体重儿的存活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早产儿存活率有较大幅度上升[1]。美国和澳大利亚第三围生保健中心20世纪90年代报道,23周出生的早产儿存活率为25%,24周出生的存活率增加至50%[2]。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ICU)中新生儿存活率为73%(55/753)[3]。
如果仅以存活时间作为标准的话,新生儿监护无疑是当今医学最成功的领域之一。然而,低体重儿特别是极低体重儿的发育和存活质量已逐渐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与此同时,早产儿的生存时间和生命质量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极度早产儿存活率的提高,存活者中主要器官损伤的报道也越来越多[1]。这些存活儿童中,常见的健康问题有支气管肺发育不良、坏死性小肠结肠炎、晶体后纤维增生症[4];轻、中度神经发育后遗症、神经发育缺陷(如脑瘫)报道率高[3]。出生体重低于750 g的婴儿预后更差,他们无追赶性生长,随着年龄的增长,各种后遗症更加明显[5]。虽然这些婴儿生命早期发病率并未增加,但在学龄期会出现许多明显的功能异常,如视觉行为综合或逻辑推理障碍、注意缺陷、持续的识别能力不足、言语水平落后等;同时,早产儿青春期健康问题如特殊性学习能力障碍、智力障碍、行为问题等也较多见[6]。从优生优育方面看,早产已失去了优生的条件。{NextPage}
2 关于早产儿救治的若干态度
19世纪上半叶,关于早产和低出生体重儿童的预后就有报道,但缺乏标准的测验方法。Hess 1922年在芝加哥成立了第一个早产儿育婴室,报告早产儿个人、家庭和社会功能,包括存活者的工作、婚姻和后代情况。20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出现定量化的指标,测定新生儿期护理和治疗过程中,由于治疗引起的伤害,主要是心理和神经感觉损伤,如认知功能低下、脑瘫、失明、耳聋和生长发育迟缓[7]。自此以后,早产儿生命质量及治疗本身对其造成的远期影响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21 两种争论
尽管已意识到早产儿和低出生体重儿发病率与死亡率都很高,96%的医生仍对这些婴儿进行积极抢救,影响他们作出决定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医生的职责”,而生命质量、法律约束和治疗费用不在其考虑范畴[8]。Schreiber等认为,对早产儿或存在缺陷的儿童进行治疗的义务不容忽视,其治疗的极限则是脑死亡。Saigal等[9]对某些极低体重儿后期的生命质量进行了研究,发现其工作、家庭生活适应良好;虽然在该领域存在很多负面报道,但研究者认为对边缘生存状态的婴儿给予精心支持治疗是应该的。
然而,SoIbach认为,从优生的角度考虑,对于有严重缺陷的儿童选择放弃是理智的,应抛开各种社会和心理因素。Campbell等认为,通过中止治疗使早产儿死亡是合法的,因为早产儿救治所带来的负担令人难以接受,对婴儿自身利益来说也无法补偿,实施早产儿的救治需要正确地处理和谨慎地记录。还有部分研究者提出,新生儿重症监护不是必然正确的,因为它只能为需要重症监护的早产儿提供很小的存活机会[10];重症治疗的负担将影响其终身受益[11]。在早产儿救治中,只有42%的父母同意采取极端的治疗方法,且大多做好了预后不佳的准备;89%的机械通气被中止[3]。
22 医学专家意见
全欧洲的新生儿专家及医护群体已形成这样一种结论:是否对早产儿进行救治,应视胎龄和出生情况而定[12]。胎龄<23周或出生体重<400 g,无脑儿或被证实有13三体或18三体综合征者不予复苏是合理的;认为如果对新生儿已无益,那么重症监护即可停止,因为治疗过程相当痛苦又难以避免死亡的结局[4]。最近资料显示,这些新生儿复苏后也很难存活或者存活伴有严重残疾[13]。心脏呼吸停止的婴儿,在15 min内无自主循环,停止复苏是合适的;心搏停止后10 min进行复苏其存活率很低,即使存活也多伴有严重残疾。对不确定的因素,包括胎龄不确定,要正确、充分评价后才能作出是否给予或继续复苏的决定。{NextPage}
法律规定也可作为是否对高危早产儿救治的依据。生命拥有最珍贵的价值,禁止终止一个无用的生命是违法的;医生的义务只有在病人脑死亡时终止救治,但在下列情况下延长生命是无谓的:不可逆转的昏迷或手术导致此类昏迷,没有机械通气就无法保证生命安全,生存有赖于经常性的重大手术或距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
23 政策和法律倾向
对极度早产儿,除了荷兰外,其他国家的医生都积极进行重症监护;但如果由于心室内出血导致临床症状恶化,各国态度就有所不同了:德国、意大利、爱沙尼亚和匈牙利主张积极治疗,而其他国家似乎都存在治疗限度问题。在英国和荷兰,父母意愿占主要地位;相对于医生而言,产科护士更倾向于终止治疗并乐于询问父母意见[14]。受法律和道德规范的制约,美国新生儿治疗草案中没有治疗限度,而在丹麦和以色列等国则允许存在限度。如果预测新生儿救治困难,他们会选择流产而不是高危分娩。这种处置减少了经济与社会消耗,减轻了卫生保健系统的负担,伦理上也是可行的[15]。英国和丹麦在流产和新生儿政策上则相对地比较自由。在某些地区,围生期有许多针对性的道德标准,包括:①新生儿有完全的道德和法律地位,而晚期胎儿只有部分道德与法律地位;②除非为挽救孕母的生命或避免出生后死亡及遭受痛苦,否则非法堕胎是不允许的;③对新生儿利益的评价应包括生理、心理、社会和财政负担等方面[16]。
目前,医学伦理学研究认为,应根据法律条文及咨询,最后决定由双亲和主治医生共同作出,同时考虑儿童的利益。临床医生起主要作用,父母的知情同意也相当重要[17]。
3 面临的伦理学问题
新生儿复苏比成年人或年长婴儿的复苏面临更大的伦理学挑战,早产儿的心肺复苏不能仅仅以是否存活作为基础,一些相关的道德因素,包括新生儿最佳预后、父母意愿、医生仁慈及无罪的责任、生命质量、卫生资源的公平利用都是首要考虑的。对患儿预后的评价应结合道德标准,理智思考“儿童最佳权益”[3]。
早产儿胎龄越小,重症监护的时间越长,遭受的痛苦越深,其远期影响也越严重[12]。新生儿重症监护的限度是什么?对处于边缘生存状态的新生儿采用极端技术是否正确?新生儿、家庭、社会,三者在最后的决定中哪种理由更充分?法律如何决定重症监护的开始、继续和终止?解决这些医学伦理学问题,需要制定特定的程序并通过实践的检验。
31 健康相关生命质量
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QOL)这一术语最早应用于社会学领域,由美国经济学家Calbraith在其所著的《富裕社会》一书中首先提出。生命质量理论与医学实践相结合,引入医学领域后形成与健康相关的生命质量(healthrelated quality of life, HRQOL),是相对于生命数量(寿命)而言的一个概念,从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分化产生,是个体生理、心理和社会健康的综合反映,受个体经历和意识的影响。目前较完整体现其涵义的有两个定义,一个是WHO的定义,HRQOL是指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个体与他们的目标、期望、标准及与所关心事件有关的生存状况体验。HRQOL测量必须以哲学和伦理学观念为前提。另一个是Levi提出的“生命质量是关于个人或群体所感到的躯体、心理和社会各方面良好状态的一种综合测量指标,是用幸福感、满意度或满足感表现出来的”。早产儿与体重正常儿童相比,HRQOL健康水平较低[18]。HRQOL低的青少年,在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住院治疗期间脑超声检查异常,则结果越严重[19]。{NextPage}
生命质量一方面是以人的体力和智力水平衡量,残疾、畸形、智力低下、白痴等都降低了生命的质量和价值,早产儿远期后遗症即说明这一点;另一方面,生命质量可以用痛苦和意识丧失来衡量。判断生命质量和价值高低主要有两个因素:一是生命本身的质量;二是某一生命对他人、对社会和人类的意义。一般认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医生应尽一切努力延长病人的生命,随着医学模式的改变,医学目的不断完善,救治的结果应该是还社会一个“完整”的人,使人在躯体、心理和社会方面适应环境,参与到健康生活之中,而不是仅具有生物学意义的生命。生命质量越来越多地受到人们的重视,适时终止救治是有益的。在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现代医学目的是预防疾病、维护健康、提高生命质量。诚然,人活着总比死了好,在医疗中尽力延长生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决不能把它推向极端,不能认为“生”就绝对的好,“死”就绝对的坏。没有生命价值可言,延长生命的过程,实质上是延长痛苦,对自身、家庭、社会并非有益。
32 权利论观点
对早产儿的挽救措施,道德与伦理更多关注生存的目的。东方人认为,人类是自然进化的产物,自然的力量与生命的变更是遵循自然规律的;人是生物链的一部分,一个未成熟的个体,甚至是一个新生儿,也是一个实体,是生命的开端,也有生命的权利。甚至胎儿也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也应获得生命的尊重。生物伦理学观点认为,生命是圣洁的,早产儿的出生也是一个重大事件[20]。
现代医学伦理学的权利论是与医学伦理学的义务论相联系的。正是因为医生对病人有义务和职责,医生相对于患者来说,就应该有特殊的权利。医生的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使其对病人尽义务的保证。权利论包括医生的权利和患者的权利两个方面,这使医生职责的必然与父母或家庭的知情同意成为可能。
父母、家庭的个人观念、意识形态、文化、宗教信仰与医疗保健专业观念及病人利益存在诸多冲突。对于医护人员来说,由于治疗和保健面对一个不可知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意愿和法律要求往往成为是否实施这种特殊治疗的理由。近年来,围生期死亡下降,但在23~35周内出生的婴儿短期或长期的影响是真实存在的,从而造成专业人员及父母在面对完全不可知的结局时的争论。尽管这些婴儿生存率上升,但却依然存在异常的可能,医生需要考虑到技术力量是否将给婴儿及其家庭带来不必要的负担,同时还要将婴儿的病情和诊断、治疗所需的代价、费用及可能出现的后遗症、预后及时地向家属或单位交代清楚,尊重他们的想法,而后综合各方面因素决定是否终止救治。医生要本着开放、真诚、乐意的态度与其父母探讨婴儿未来利益问题,以避免学科、医生和家庭间的尴尬[21]。
一般认为,对早产儿不予复苏或后期停止复苏在伦理上是等效的,后期可能为收集更多的临床信息来与其父母、家庭协商提供时间。总的来说,延迟、定级和部分支持治疗是无益的;即使婴儿存活,其预后也因这种治疗手段变得更糟。新生儿重症监护可能造成损伤或失能,治疗引起的损伤包括脑室周围出血、脑室周围白质软化、早产儿视网膜病变、氧气依赖性延长、脑唤起反应异常。这一切,又为作出早产儿是否救治的决定增加了新的难度。{NextPage}
33 生命价值和生命时值
生命的时值是生命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是生命的目的与归宿。生命质量、生命价值和生命时值是构成生命的3个基本要素。20世纪50年代以来,医学对生命的控制能力日益增大,当生命价值不可逆地丧失后,仍有能力继续维持生命的时值,于是,医学切断了生命价值与生命时值的必然联系,引起生命基本要素之间关系的分离。医学这种对生命完整性的破坏及只注重生命的时值而忽视生命的价值,是引起人们关注生命质量和价值的根本原因。
生命价值是生命自身的构成要素,是生命的重要内容,所以生命神圣并不只是生命的时值神圣,也是生命的价值神圣。尊重生命并不只是尊重生命的时值也要尊重生命的价值,尊重生命的完整。当代人们对生命质量和价值的重视,正是这种对生命内涵的全面认识和对生命整体性尊重的体现。
传统的医学伦理学绝对强调生命的神圣,片面追求生命数量。临床治疗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和延长病人的生命,而且更应重视和努力提高生命的质量。不注重生命质量和价值的治疗观点,在道德观上是不全面的。因此,临床医生在考虑治疗方案时,在首先考虑保全病人生命的同时,也应考虑并力争保证最好的生命质量。在早产儿救治过程中,这种思想更应贯穿始终;不仅要努力提高早产儿的存活率,更多地要考虑这种救治的意义何在及对儿童后期影响如何。
安乐死的宗旨是减轻或消除死亡痛苦,维持人的尊严,因此,是对生命质量和价值的尊重,而不是对生命的破坏。一味延长生命的时值而不考虑生命的价值,是对生命完整性的破坏,是对生命的亵渎。医生的人道主义,既是一种医学行为,也是一种社会学行为。社会学行为的出发点应该有利于社会。建立生命的神圣论、质量论和价值论相统一的生命观,才是唯一正确科学的生命观。在这个前提下医生终止救治的行为是人道主义的另一种表现,它有利于患者家庭、社会,也有利于儿童自身。
正确理解生命质量和价值与生命神圣的关系,不仅有利于树立正确的生命道德观,而且还为当代医学解决了早产儿救治的伦理问题,又为保持传统的尊重生命色彩提供了可能。
 妇产科在线APP下载
妇产科在线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