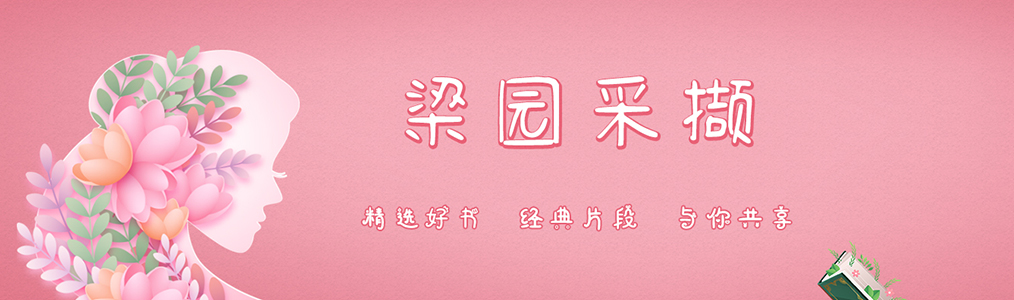女性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pelvic floordysfunction,PFD)是表现为子宫脱垂等盆腔器官膨出(pelvic organ prolapse,POP)和压力性尿失禁(stress urinary incontinence,SUI)等一系列盆底损伤与缺陷的疾病。随着我国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和人们对生活质量的日益重视,PFD的发病、预防及修复与重建逐渐受到关注。盆底支持和缺陷组织基础研究的深入、新的理论的建立、盆底组织修复观念的更新,女性PFD的治疗策略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一、PFD的流行病学现状与预防
有别于其他妇科疾病,部分PFD诊断是可以通过问卷方式来明确诊断的,这为该类疾病的流行病学研究提供了有利条件。问卷调查已沿用多年,问卷的种类也多种多样,并经临床应用后已日臻完善。
国际尿失禁咨询委员会(intemational consultation onincontinence,ICI)对世界范围内已有的流行病学资料进行的荟萃分析发现,大部分尿失禁患者都集中在老年妇女,尿失禁妇女的中位年龄为50—60岁,妇女的患病率为10% 一40% 。美国的资料显示,尿失禁患者的治疗费用为平均每人每年105美元,这是首次对这类患者治疗费用的调查结果。但目前普遍认为,现有的流行病学调查数据明显低于实际的发病情况。我国现已开展了部分地区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如对北京市城区和郊区(包括农村)采用整群分层方法,随机抽取20岁以上5300例成年女性进行的“国际下泌尿道症状问卷”调查结果分析发现,北京地区成年女性尿失禁的现患率为38.5% ,其中半数以上为SUI。目前,已开展的全国范围内尿失禁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有望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中国自己的流行病学资料,裨益于国家相关政策的制定。
尽管已有POP定量的标准化命名法,但不同检查者对同一患者盆腔的测定结果也可能有差异,从而影响其诊断的准确性和一致性,所以关于POP定量分析的流行病学报道也较少,较大样本量的报道为荷兰一城镇45—85岁的2750例妇女的问卷调查及与之相结合的临床检查,结果显示,在这组人群中,40%患有Ⅱ一Ⅳ度的POP。
对PFD发生的危险因素研究,北京地区的流行病学研究结果发现,年龄、阴道分娩、多产次、高体重指数、高血压(以舒张压升高为主)、饮酒、便秘、慢性盆腔痛是成年女性SUI发病的危险因素。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流行病学研究资料也提示,阴道分娩是PFD的独立危险因素。另有研究报道,剖宫产对PFD的发展有保护作用。近年来,三维或四维盆底超声检查及MRI研究多提示阴道分娩对肛提肌有损伤,以耻骨宫颈肌肉从盆壁撕裂最常见,而这些因盆底损伤所致的SUI和POP在产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以恢复、甚至自愈。提高产科质量、及早处理阴道难产和滞产、对孕晚期已有PFD的患者适当放宽剖宫产手术指征、产后及时进行盆底肌肉康复训练,对减少PFD的发生有着积极的预防和治疗作用,值得进一步关注。
此外,尿失禁和POP有普遍的诊治滞后问题,所谓“难言之隐”严重影响妇女的健康和生活质量,所以应加强公众宣传,引起重视,早诊早治。
二、无症状POP的处理及非手术治疗的价值
目前,国际上尚缺乏广泛认可的对POP临床诊断的标准定义。现推荐的定义为:任何有生殖道膨出表现的生殖道支持组织缺陷,膨出的最远端超出处女膜缘。相对于有症状的重度POP患者进行手术治疗有良好预后而言,到目前为止,尚没有循证医学的证据表明对于无症状(屏气下未超出处女膜缘)的POP患者实施手术能够改善预后和预防疾病进展,也不能预测哪些无症状POP妇女可能会出现症状加重,或多长时间可能发展为有症状的重度POP。因此,对于无症状的POP妇女给予外科修复是没有必要的。鉴于这一基本观点,对于无症状的POP妇女的手术干预一般情况下并不推荐,选择观察与建议非手术治疗应该是合理的处理方案。可以这样说,我们目前没有得到患者需要早期临床干预的循证医学证据,所以没有理由因为要预防POP症状出现或是推测其可能会变得更严重前采取手术治疗。
对于无症状的POP妇女,改变生活方式的建议可能降低她们发展成有症状POP的可能性,这些建议也符合健康生活方式的一般考虑。生活方式的干预如下:(1)足够的水量摄入,并且有正确的排尿习惯;(2)调整饮食,增加水和纤维素摄入;(3)调整排便习惯,以保证肠蠕动规律而排便时不需过分用力;(4)避免过多的负重和用力;(5)降低体重,减少吸烟;(6)对伴发疾病如糖尿病、咳喘、便秘等进行有效的治疗以减少对盆底功能的影响。对于有症状的中度POP,在临床检查POP程度与患者非常严重的盆腔压迫感的主诉不符的情况下,建议放置子宫托进行试验性治疗,如果主诉症状缓解,患者就可以选择继续应用子宫托,这可以被认为是POP的一线治疗,而且有较好的患者依从性。
非手术疗法还有盆底肌肉锻炼、生物反馈指导的盆底肌肉锻炼、电刺激、磁刺激治疗等方法。目前普遍认为,联合治疗的方法优于单一治疗方法,对产后发生的POP采取非手术疗法,效果确实且副作用小,尤其是生物反馈+盆底电刺激治疗的总有效率高达90%。对分娩后1年以上仍然存在SUI的患者,非手术疗法仍安全、有效。
2007年,Hagen教授对世界范围内的非手术疗法的报道进行荟萃分析发现,非手术疗法对POP有较好的治疗效果,并认为非手术疗法可以达到预防盆腔器官脱垂加重,减轻症状,增加盆底肌肉的强度、耐力和支持力,避免或延缓手术干预时间的目的。在近年各种盆底重建手术蜂拥而至之时,提出非手术疗法的适应证、方法和重要性是必要的。
三、盆底重建手术的评价和选择
PFD的手术治疗方法繁多,但各种手术疗法的效果均不理想,主要原因是因为盆底修复及重建手术的复杂性和多样性。2004年,Maher教授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盆底修复手术的循证医学分析证明,传统的阴道前壁修补术和后壁修补术有较高的复发率。
目前,国际上广泛认同PFD治疗的最新理念为1992年De Lancey教授提出的盆底支持结构3个水平的理论:第一水平支持为上层支持结构,由主韧带、官骶韧带联合组成;第二水平支持为宫旁和盆壁支持结构,由肛提肌群、直肠阴道筋膜和膀胱阴道筋膜组成;第三水平支持为远端支持结构,由会阴体、尿道括约肌和肛f-j阴道筋膜组成;De Lancey教授还提出了盆底功能重建的生物力学要求为:第一水平重在悬吊,第二水平应加强中部一阴道侧方支持,第三水平主要进行远端融合。对PFD的治疗应强调整体理论,即盆底功能障碍首先是由于其解剖异常,进而发生功能障碍,最终引起各种临床症状。因此,治疗的基本点是用解剖的恢复达到功能的恢复,其精髓重在“支持”和“重建”。治疗前应对盆底功能,包括对肌肉、结缔组织和神经支配的平衡及其损伤程度做出诊断和定位,然后进行分区域(前、中、后盆腔)的缺陷修补。
近年来,随着对盆底解剖认识的深入、手术器械的改进以及修补材料的发明和应用,涌现出许多重建手术方式,治疗效果也在不断提高。但这些手术方式尚处“年轻”阶段,尚有复发和并发症发生等问题,尤其是吊带和补片的侵蚀、暴露、感染及对性功能的影响,有待积累资料进行临床循证医学的证据证明。正确评价和明确各种手术方法的适应证尤为重要。PFD的治愈标准已由传统的单纯立足于一系列的客观检查和医生确诊的“客观治愈率”过渡到兼顾关注患者术后症状和生活质量改善的“主观治愈率”,许多生活质量评分及针对术后症状、性生活质量的问卷调查已作为PFD手术后随访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女性盆底学研究方兴未艾,2004年3月在福州召开了第一届女性尿失禁及PFD学术研讨会,2005年12月成立了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女性盆底学组,2007年4月在成都召开了第二届全国女性盆底学学术会议,反映了我国女性PFD从基础到临床的深入研究和快速发展。同时我们要不断更新和接受新的观念和理论,采纳国际化、规范化的诊断和治疗方法,也要结合中国国情,探索适合我国该领域研究发展的道路。对目前开展的经阴道、经腹、经腹腔镜路径的盆底修复和重建手术,孰优孰劣还有争议,需要根据术者的手术技巧和熟练程度、知识和经验以及患者的需求而定。

 妇产科在线APP下载
妇产科在线APP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