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dreas Thurkow
荷兰 阿姆斯特丹 妇科学术咨询中心
评语:Andreas Thurkow博士,他是一个超前于时代的人,是荷兰宫腔镜技术的先驱之一。起初,他是一个“被误解的天才”。
问:你对宫腔镜越来越感兴趣吗?原因是什么?
答:是的,我对宫腔镜越来越感兴趣。八十年代初,我开始做宫腔镜检查,但同事们认为我是一个无害的白痴,在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其益处的情况下,开展无用的手术,这与现状相去甚远。尽管宫腔镜检查已经被认为是常规检查,特别是宫腔镜检查及手术都越来越多地在门诊环境中进行,我仍旧对诊断性宫腔镜检查以及宫腔镜手术越来越感兴趣。当然,现在专家们都能够进行相关操作,但是技术和仪器降低了入门门槛,甚至经验较少的人也可以进行操作。更多的同事现在意识到这项技术的重要,在许多国家,住院医师培训中已经开展了宫腔镜技术的教学。
话虽如此,我仍然惊讶地发现,在一些国家(如美国),宫腔镜技术的应用仍然比其他工业化国家要少得多。我非常愿意积极地帮助开展教学活动改变这种状况,因此我非常荣幸能够参加豪洛捷(Hologic)的全球指导委员的门诊教学倡议(Office Education Initiative),该委员会致力于改善这个问题。
问:你认为宫腔镜绝育术的前景如何?
答:啊,宫腔镜绝育术的前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当然,现在我们所有的人(病人,医生,保险公司、权威机构等)都非常害怕Essure崩溃的重演。但我衷心希望我们最终能够找到一种不像Essure那样造成迟发效应的装置,并且我们能够以真诚的方式与我们的患者讨论该装置。虽然在大多数病例中,我们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许多妇女的似乎与Essure装置有关的这些问题。尽可能地取出所有组成部分是符合逻辑的,理论上并没有在身体中植入任何部分。遗憾的是,在腹腔镜和宫腔镜绝育方法之间仍然存在明显的侵袭性差异,并有关于相应的并发症发生率的科学证据。这尤其适用于那些有腹腔镜禁忌症的患者(例如,既往手术史、凝血障碍)。
我知道有几种系统和设备可能成为Essure的替代品。在这些(我知道至少有4个系统)中,Altaseal是未来最有可能性的,因为它在临床结果方面拥有最多的数据,其中大多数是我作为研究者收集的。
问:培训课程和亲手实践操作对初学者来说非常重要。你同意吗?
答:我绝对同意这个说法!在我看来,在开始在实际患者上使用该技术之前,必须学习宫腔镜检查所需的眼手协调以及在模型上熟悉手术所涉及的器械。我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试图执行这些无用的练习。不幸的是,几年前,我中心出现了一个严重的并发症,这使其他人相信这种练习的必要性。此后,它确实成为一个先决条件,阿姆斯特丹大学中心的所有附属医院,其中不具有这个条件的医生就不能再执行任何类型的宫腔镜检查手术。
问:根据你的经验,进行宫腔镜手术最困难的是什么?
答:最困难的宫腔镜手术可能是宫腔镜下宫腔粘连松解术,尤其是当宫腔结构完全消失的时候。这类Asherman病例的相对稀少,明显增加了对这种类型手术的集中需求。我在1982年的培训期间开始进行这类手术,在培训结束时,我已经做了50例这类手术,当时在我进行培训的Groningen大学医院(超过100万居民)周围非常广阔的地区,没有人具有这样的宫腔镜操作经验。
可能第二个困难的宫腔镜手术是切除4厘米或更大的,且深达子宫肌层的2型肌瘤。为了防止过度水化和穿孔,需要结合各种技巧:对子宫进行完美的三维评估,眼手协调进行绝对良好的控制,同时具有足够的速度在发生严重并发症之前结束手术。我采用了一种提高速度的新技术,即把肌瘤切成几部分,并尽可能地去核除,一旦达到最大程度,就可以在经直肠超声引导下切除。超声引导可以监测肌瘤和浆膜之间覆盖的正常肌层厚度。
有趣的是,直到我使用这种切除技术已经好几年了,才意识到其他人(例如Ivan Mazzon医生)也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显然,好的想法往往几乎同时出现,而且彼此独立。另一个例子是Mark Hans Emanuel 医生和 Guiseppe Bigatti医生在宫腔镜中对于矫形手术刨削器的应用,似乎也一直是独立发展的。
问:对于刚开始从事微创妇科手术的年轻医生,你有什么建议吗?
答:我给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年轻医生的建议就是像我过去做的一样去做:即使你可能偶尔在路上遇到障碍,也要保持动力,专注以及耐心。正如我之前所说,在80年代,我经常被看做是有点疯狂的,在“玩弄”那些没有任何科学证据证明具有任何用途的技术。COBRA奖是每两年颁发一次的奖项,颁给为荷兰妇科领域手术的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医生。在2014年获得这一奖项后,我在致谢演讲中特别提到这些激励性的话语,以此来激励年轻同事们。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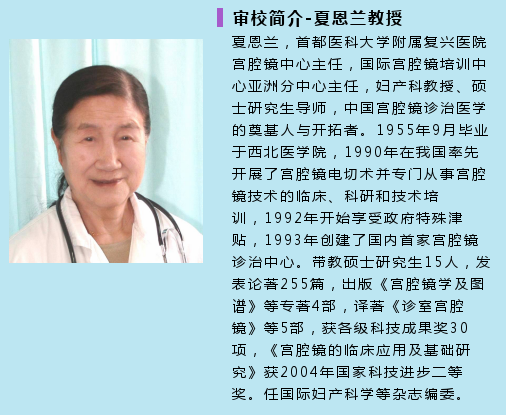

 妇产科在线APP下载
妇产科在线APP下载













